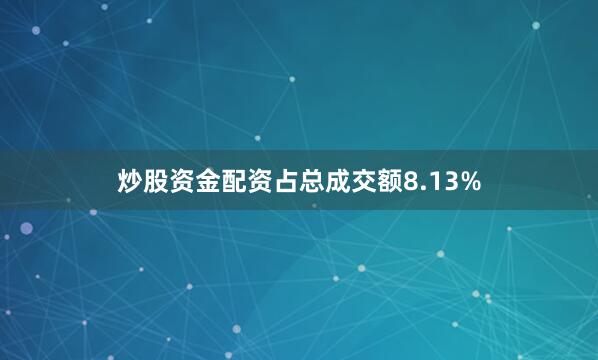金华老人李仲明的左腿膝盖往下,像是被开水煮过一样,没有完整的皮。大大小小的烂坑脓血模糊,深浅不一,有的烂到露出骨膜。揭开创面上随便捡来的包装广告纸,就会看到烂坑里绿色的霉毛。
这是让南香红印象最深刻的一双烂脚。战争已经结束了70年,但在浙江多个曾遭遇疑似细菌战武器炭疽、鼻疽攻击的村庄,一双双烂脚仍在流脓流血,无声控诉着那段被掩盖的历史。南香红说,“某种意义上,烂脚就是战争创伤具象的体现。”
2002年,时任《南方周末》记者的南香红,因执行采访任务,见到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南香红对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的人体实验有所耳闻,但几乎不了解日军在中国战场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历史。彼时的她也不曾想到,这次采访会牵引她跨越23年的时光,架构起一部长达64万字的非虚构著作——《没有结束的细菌战》。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这是南香红从王选口中听到最震撼的一句话。面对这一遗痛至今的历史“黑洞”,连抽身离开,好像都构成一种残忍。此后的23年,她深入浙江金华、衢州、丽水、义乌、湖南常德等地饱受细菌战蹂躏的村庄,记录下幸存者的声音;远赴日本法庭,追踪王选带领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的艰难历程;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史料,打捞起一个个尘封的个体生命故事。那些疼痛和罪责被刀笔刻录在书里,是这位记者亲眼所见的证据。
展开剩余94%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南香红是中国最早倡导、实践和探索新闻特稿和非虚构写作者。她以丰富扎实的作品,建立起非虚构写作领域的影响力。如今,从记者再到非虚构作家,她的身份转变,也诠释着她对于王选“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这一理念的践行。
深度训练营与南香红展开对话,在她的讲述中,我们得以回望这场耗时23年的、漫长的跟踪报道。我们试图挖掘她在采写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探讨这本书背后所承载的、超越个体努力的职业精神,以及追寻历史真相的社会意义。
南香红
以下是「深度训练营」与南香红的对话:
Q:面对“细菌战”这样严肃而沉重的话题,您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接触的?
A:那是2002年。当时,《南方周末》编辑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采访王选,当时她是细菌战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原告团团长。此前,我只知道731部队的存在,但对于细菌战的具体细节并不了解。那次采访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第一次知道,鼠疫这种特别恶性、极具传染性的疾病,居然被用作战争手段,作为战争武器进行攻击,还造成大面积的流行。这让我感到难以置信。
过去,我们都知道鼠疫曾在中世纪的欧洲流行,造成一半人口死亡。因此,我一直觉得鼠疫是一种特别可怕的疾病。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鼠疫患者,只是从小说或资料里看到过一些描述,但它到底有多可怕,我并不清楚。而那次采访,我主要围绕王选的家乡崇山村展开,听她讲述亲人和乡亲们如何死于鼠疫。这些真实的故事对我产生了巨大冲击,我觉得这是特别重大的事情。
当时的采访安排比较紧凑,我和王选只有两次见面交流的机会,随后便需要尽快完成稿件,以满足版面需求。由于时间紧张,我没有机会亲自去崇山村实地探访。但这个遗憾也在我心中埋下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要有机会到崇山村,与村民面对面接触。因为那里是新闻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更深入地了解真相。这也成为我后来多次前往崇山村采访并持续关注这一话题的重要契机。
王选在崇山村故居前
Q:过程中,哪个关键契机让您意识到这个话题不仅值得深入探究,而且有必要花大量时间去撰写这样一篇长篇非虚构专著呢?
A:其实这样的契机挺多的。2005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组关于细菌战的长篇报道,这也是我后来出版的《王选的八年抗战》一书中的部分内容。从2002年采访完王选之后,我就一直有个想法,去崇山村,去当年细菌战的战场看看。后来,这已经不是《南方周末》的选题了,而是我自费利用业余时间,沿着浙赣线去看了当年遭受细菌战攻击的地方。
另外,到了2015年,我又想重新梳理这个选题,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持续发展的事件。特别是2011年,新的资料出现了。此外,我在采访过程中也遇到大量“烂脚”的人,这些人从战争时期一直烂到现在,疑似是炭疽感染造成的。
由于王选对烂脚的持续调查和媒体的报道呼吁,有几位院士出来担当“烂脚”治疗工作,看到治愈的希望,但资金上比较缺乏。所以我们借助腾讯公益发起了治疗“烂脚”公益项目,那一年,我在腾讯新闻上连续发了八篇报道,就是为了保持新闻的热度,让更多人了解并捐款。最终筹集200多万元,治好180多位老人。这些事情让我觉得细菌战远没有结束,现实中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关注。
所以,2015年我又开始重新采访,重走当年细菌战发生地和细菌战诉讼发起地,去记录原告和受害者的口述历史,去探访“烂脚”患者。再加上这些年来积累的和日本人的接触经历——其实从细菌战的揭露到诉讼发起,再到对细菌战诉讼的支持,都离不开一些日本人的帮助,他们做出很大贡献,而这一部分在我之前的报道很少涉及。所以,我想把这些内容写完整,把整个事情梳理清楚。于是从2015年开始,我又重新投入采访和构思这本书,一直持续到现在。
南香红在义乌市崇山村采访
Q:您此前提到,最初见到王选时,她讲了一句让您印象深刻:“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王选对于您的调查影响大吗?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A:这句话是我第一次采访她时听到的。她当时就说:“这么邪恶的一件事,怎么能放着不管?看到了这些人的苦难,你怎么能不为他们去做点事?”所以她说:“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作为战后一代人,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但她坚信历史不是一个遥远的过去,而是会与我们迎面相撞,影响到现在的生活。所以她一直强调“历史是可以看见的”。她的这些观点对我影响很大,整个调查过程都是在她的推动下展开的。
包括后来新资料的发现、“烂脚”的治疗和调查,还有她做的田野调查——比如山东卫河流域的调查。日军曾扒开卫河河口撒播霍乱,造成百万人以上的伤亡。王选他们调查了卫河流域老百姓的口述历史,整理成了一本12卷的口述历史——《大贱年》。从这一系列行动来看,她从未停下自己的脚步。一旦有新发现,她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也希望我能去帮助他们呼吁。所以她一直在推动着我,让我持续关注这件事。
王选和大学生在调查烂脚
Q:长达二十多年的创作过程中,您对细菌战的理解发生了哪些变化?
A:刚开始接触时,面对这一特别恶劣的事情,刺激是特别大的。但随着采访不断深入,我对于这个重大主题的认识和把握,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我写的内容也体现了一个从对细菌战几乎一无所知,到逐渐了解细菌战的过程是和原子武器一样具有毁灭人类的非常规武器。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2005年,《南方周末》出细菌战特刊,我平时在北京工作,那次是特意为这个特刊来到广州编辑部,编辑对我说:“南香红,你不如自己写个编者按吧,你可能认识更深刻一些。”
细菌战和原子弹一样,都属于非常规战争手段。这种战争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以枪炮、飞机、航母等为主的钢铁对撞式的战争,而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手段。原子弹一扔下来,产生巨大的爆炸,甚至瞬间一切将钢铁、水泥雾化,其威力远超任何炸弹,是人类无法想象的武器。同样,细菌武器也和原子弹一样,产生的效果非同一般。它看不见、摸不着,有多种菌种和传染病,通过秘密手段投放,无论是地面投放还是空中撒播,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对大面积的人类、动物、植物乃至所有生命体造成毁灭性打击。而且这种打击是绵延不断的。
比如衢州被投放鼠疫后,从1940年开始防疫,一直持续到1948年,年年都有鼠疫复发。这相当于在正面战场之外,还有一场秘密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为人知,既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也不为世界大多数人所知。1948年衢州解放,新中国的防疫队伍接手,一直在进行防疫工作,直到现在,一些地方仍需不定期抽查,检查鼠疫指标是否超标。而且有些年份的数据仍然超标。细菌战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
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觉得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恶劣的一种战争手段,会对人类造成毁灭性打击。同时,日军在二战期间的细菌武器攻击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地用于战争的实战攻击案例。从这个角度看,细菌战的意义和深度与我最初认识到的鼠疫流行、民众的苦难和死亡有很大不同。再回看细菌战诉讼,就能明白那些180名原告在中日民间合力下,到日本去诉讼,最终让日本法院承认细菌战是历史史实,并认定日本国家违背国际法,是反人道的行为,具有国家责任的意义。
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反复琢磨一个主题,不断重新认识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Q:正如您此前所说,在调查和创作过程中,您既看到人性的黑暗,也看到人性的至善,这种强烈的情感变化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A:一开始,我心理上不太好接受,因为很多事特别恶劣,让人会产生生理上的不适。比如看到那些“烂脚”,伤口鲜血淋漓,臭气熏天,我觉得任何人都难以直视。
我在写书之前,自己也不太了解细菌武器投放后的具体后果,所以我去查找了一些资料,比如参考日本核爆后的非虚构书籍和纪录片。其中,《广岛》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它通过几个人的故事,展现了核爆后的场景,有些细节令人难以想象。当一个人想去拉另一个人的手将她扶起时,对方整个手臂的皮肤像脱手套一样脱下来。这种细节如果没有深入了解,是很难想象的。
细菌战也是如此,如果不深入研究,你就不知道鼠疫死者是什么样子。鼠疫死者身体会卷曲,肌肉和筋腱收缩,全身变黑,这就是“黑死病”的由来。在常德等地,当地百姓从未见过鼠疫,也没有鼠疫流行经历,当他们看到家人这样死去,就以为是触犯了神灵,或者是上辈子没行好,这辈子受到报应。他们甚至会在夜里到田野里敲打树丛,呼唤死者的名字,试图为他们“叫魂”。你可以想象那种场景有多恐怖。
但与此同时,我也接触到很多人,他们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比如书中提到的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曾任日本律师协会的会长,是日本法律界的精英人士,他讲述的他经历战争的故事。他是一名日本的海军士兵,他在战争中曾面临亲手处决美军飞行员的命令,但最终是由另一位少尉执行了斩首。战后,那位少尉自杀了,而他则反思战争,意识到战争的本质是杀人与被杀。
卸任日本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后,加入细菌战诉讼团队,当时已经72岁。他不是挂名的团长,而是每次都亲自出庭,全程参与了40次庭审。他承诺他要用余生陪中国受害者将官司打到底。期间他患了癌症,一直瞒着大家,坚持出庭,最终实现了他的把官司打到底的承诺,诉讼结束两年后他就去世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作为一个日本精英律师,完全自愿地为中国受害者服务,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所包含的人性的力量,人间的善的力量。这种善举,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和故事展现出来的。
正是这种善恶之间的较量、交织,就像战场上的对决一样,让细菌战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清晰。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坚持不懈地调查和追究,细菌战可能仍然是历史中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就像日本遭受原子弹爆炸后,日本民间团体从战后一直到现在,不停地去调查,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伤亡,原子弹的威力有多大,对自然、人类和环境造成了怎样的破坏。他们不停地向世界诉说,最终让原子弹的伤害变得清晰,也让反核成为人类的共识。
相比之下,细菌战因为长期被忽视、被遗忘,一直没有像核爆那样被清楚认识。正是因为这些年包括王选在内的许多人的努力,细菌战才逐渐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变得清晰起来。
Q:日本人的角色在细菌战中有非常明显的善恶对冲体现,您刚刚也提到这些年和日本人有了更多接触,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
A:刚开始接触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接触过日本人,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只有一个主角,就是王选,许多媒体也都是围绕着王选进行报道。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形成合力的事件。
细菌战是日本人犯下的罪行,但战后最早睁开眼睛反思战争的,也是日本人。从1945年之后,日本就逐渐形成了反战的潮流。20世纪70年代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后,日本的第一批记者来到中国,开始报道南京大屠杀。当他们将日本军队在国外的战争犯罪,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报道出来后,更多的日本市民开始到中国或者东南亚地区进行调查,依据调查的事实去反思战争,教育更多的人。
最早反思细菌战的也是日本人,他们比中国人整整早了20年。是日本人首先来到义乌崇山村调查当年的情况,他们的到来正好和崇山村人想告日本的想法契合,于是才有了这场诉讼。
日本每一个具体参与的人,都是自费来到中国进行调查的。日本有许多市民团体支持受害者到日本申诉。举个例子,当他们为中国受害者募集资金时,会在会场里传递一个纸袋子,这个纸袋子从主席台上传下来,传递给每一个人,如果愿意的话就往袋子里放一点钱。这些钱最后汇集起来,就可以支援一次慰安妇到日本举证,赞助细菌战的受害者到日本举证,或者用于给市民做战争的展览。
又比如在开细菌战的学习会和研讨会时,大家会选择一个市民活动的场馆,提前发出广告,下班后坐地铁过来开会。有时大家都没有吃饭,有的人就带一些零食,大家一边吃一边开会。开完会后,每人走的时候会在门口的盘子里放下3000或5000日元,用来支付会场的租金。这种运作方式很市民化,全部都是市民自愿、自费的,更不用说刚才提到的那些支持的律师了。
包括在细菌战开庭之前,这些市民组织还会提前去给大家做动员,希望更多的人来到法庭。因为开庭一般都是在工作日,实在人少时,他们就坐得松散一些,让法官觉得有人在法庭里旁听,不会太冷清。当中国受害者去了以后,他们还会事先制作好写着标语的牌子,大家挂着牌子到街上去游行,为了让更多日本市民知道、看到,从而造成影响,等等。类似的都是非常小的小事,没有什么激昂的举动,但你就会看到大家默默地努力,去尽一点力量帮助中国受害者的行动。
Q:这本书有60多万字,在您写作过程中,是如何把海量的材料组织起来的?
A:这确实是非常难的,材料确实太多。这本书目前呈现了65万字,但在写作时,文字量达到80万到100万字,经历了大量的修改。光是和王选一起校对修改,就经历了五个版本,更不用说我之前写到一半再推翻的情况。
关键是,这么多材料,每一个都需要去核实。这是非虚构作品的要求,不能写得不真实或者有瑕疵。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事实下面都有注释,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内容是可以查证的,不是想象出来的,也不是编造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可考的。而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以前我们写特稿或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时候是不需要加注的。好像记者就是一个发布者,因为我是记者,所以就是真的,你就相信,似乎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但写一部著作就不一样了,事实的核查是非常重要的。在事实核查的基础上,你还要找到事实和事实之间的联系,能够把它们组成一个故事,然后让它好看。这些都挺难的,也都是我以前所没有遇到的。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反复学习的过程。
Q: 您在第五部里大量地写了“烂脚”人的生存状况,有什么考量?
A: 烂脚这个事能够得到治疗,是非常欣慰的。当王选知道烂脚可以治好的时候,她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到了一种自细菌战诉讼以来从来未有的幸福感。烂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战争创伤具象的体现。烂脚是战争遗留至今的一个“伤口”,这个“伤口”能够通过治疗得到抚慰,除了有具象意义之外,还有象征意义。
能够让这些老人在晚年放下沉重的战争创伤,比较安详地到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凡的。
Q: 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位因为“烂脚”身心受到严重影响的老人?
A: 我书里写到柴长庚的故事。我去养老院采访他时,他已经84岁,刚刚结婚,他的老伴94岁。他一辈子都没有结过婚,只因烂脚,无人愿嫁。于是,他孤独一生。而那家养老院,只有孤寡老人才能入住。我去采访时,他特别高兴,说:“你看,我们结婚了。”他的老伴原本也是孤寡老人,住在养老院。他们在养老院相识,结为伴侣。他还从柜子里翻了半天,拿出结婚证给我看。结婚证上的他,满脸笑容。你们能想象结婚照上的人满头白发吗?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还有李仲明的烂脚,烂得太厉害了。他也是一辈子孤寡,没有家庭。医生想给他治疗,他却不愿脱衣服,哭闹不止。经过治疗,他的伤口基本痊愈。然而,回家后无人照料,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溃烂。王选呼吁,这不仅是一个治疗问题,更需要系统地照顾他的生活。于是,她在群里号召志愿者帮忙。后来,当地一位退休领导组织人定期为李仲明换药。直到他去世,双腿都保持着干净。这些事情让人感慨万千。从战争期间一直烂到如今,这伤口世上罕见。
Q: 对于他们而言,“烂脚”是一辈子的伤痛。您在接触他们的过程中,他们愿意和您聊这些经历吗?
A: 有的老人在我们去看望她的时候,状态显得很木讷、很呆滞,基本上不与我们交流,眼神也不与我们对视。当我们去给他换药,扶他出来坐在院子里时,他也不吭声。但有的老人就不一样,当我们去与他交流时,他还是很高兴的。毕竟有人来看望他了,有人来关心他的情况,他也很愿意与我们倾诉。不同老人的精神状况确实不太一样,差异还是挺大的。
Q: 书中提到一些已故人物的故事,您是怎样去了解这些事实并进行交叉验证的?
A:比如书中提到的土屋公献我就没采访到,他生前是律师团团长,因为我2002年时才介入这个选题,一开始也没有机会去日本和他们有接触,后来土屋公献去世了。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根据跟他接触的人去还原拼凑起来的,比如王选、跟他接触过的原告、他的自传等等。细节都是通过讲述得来的,你需要在采访中去追问,让讲述者把它还原出来,这些方法跟我们平时采访的方法是一样的。
Q:现在回顾整个写作过程,有没有一些能够让我们学习借鉴的非虚构写作方法论?
A:非虚构写作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可能是需要明确一个标准的。现在,由于“非虚构”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很多人都声称自己在写非虚构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
另外,非虚构写作也有一些方法可循。非虚构毕竟不像学者的学术著作。从某种角度来说,它还是需要有故事的,这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事实明确清楚的基础上,还要讲好故事。写作时要有故事构架,要有情节,要有场景,要有细节,等等,这些故事的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另一个方面是注释、参考书目等。什么样的书、资料是可信的?什么样的信源是可以采纳的?什么样的信源是需要考证和质疑的?这些问题可能也需要有标准。我觉得研究者可以将这些标准列出来,比如一级信源、二级信源、三级信源分别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源是不可用的,或者需要高度怀疑的?这些规律是可以去总结的。
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现场采访、资料应用、档案使用等的比例如何把握是比较恰当的,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档案材料的使用方法也很重要。你不能让它成为讲故事的障碍,不能让它成为故事中一个个的疙瘩,让读者读起来感到困难。你需要合理地将它们化解。这些技巧也是可以总结的。其实从学界的角度来说,可以从一部著作、一个写作者的实践中去总结一些规律和经验,这是需要更多人去做的事情。
Q: 这本书的结构是如何编排的?
A: 这本书的结构其实也调整了很多次。材料很多,从哪里开始、如何架构,都是需要反复琢磨的问题。我最初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比如我写20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情,写四十年代细菌战攻击的事情,写1945年日美交易的事情,还有细菌战诉讼的事情,这些内容在时间上会有断裂,很难串联起来。
所以,我后来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用王选来串联。以“看见”为线索,从王选看见,到日本人看见,再到所有人看见,然后力量集合在一起,发起这场诉讼。通过这场诉讼,他们又去现场调查,进而发掘出更多细菌战的事实,把细菌战揭露出来,最后以细菌战诉讼的发起与结束,以及伤口的疗愈,完成一个闭环。
至于“引子”部分,一开始并不是放在最前面的。我最初是从第一部第一章描写王选回乡这部分开始的,但后来觉得这样进入主题太慢。读者会疑惑:这个人到底回乡干什么?这个人又去找日本人干什么?没有一下子抓住主题。于是,我把后面的一部分内容提前,作为“引子”放到前面,做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
Q: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这本书创作和出版过程中,有没有留下哪些遗憾?
A: 遗憾还是不少的。我在最后校对的时候,发现还是有一些内容可以删减的。比如,这本书如果去掉5万字,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影响整个主题的表达。现在这本书又做了第二遍校对,把里面出现的一些错别字或者不太恰当的地方又做了调整。也许在加印的时候,这些问题就能改过来了。
书或者新闻作品,很难达到100%的完美,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只有写完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如果这样调整会更好。修改和完善是没有止境的。如果后续有更多关于细菌战的事实或者新的新闻发生,我肯定还会持续关注的。我也期待这本书的再版,或者什么时候能做得更完善一些。
Q:跟踪报道细菌战这么多年间,会有某一刻想要放弃写作这件事的念头吗?
A:其实,我并不是一直都有动力的。因为做记者总是要应对各种各样的选题,不可能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这本书里,所以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放下了,有一段时间可能就不会去动它。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遇到了障碍,或者不想去面对,当然忙也是一个原因,它有时候也会成为一个借口。所以,做做停停的情况还挺多的,确实不可能一口气做完,那样也确实会吃不消。
但对于搞写作的人来说,不去写它并不意味着不去想,也不意味着心里没有在酝酿。所以有时候也会朝思暮想,比如晚上睡着或者半夜醒来的时候,也会去琢磨。一旦找到一个方向,或者找到一个灵感,可能又会重新开始。大概就是这样搁搁停停的一个过程。
Q: 细菌战与其他灾难报道/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A: 细菌战本身确实是一场灾难,我觉得它与其他灾难性事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平时我们做的报道是新闻报道,新闻的重点是围绕当下发生的事情、事情的背景以及后续产生的影响,把这些内容讲清楚,这是新闻需要做的。
细菌战报道与一般新闻报道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新闻报道和非虚构写作之间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公共卫生领域的报道不能写成书。如果要写成书,就需要在深度、广度以及讲述方法上做更多的工作。
Q: 您在书中多次提到“中国的历史书写中缺少个体的记忆”,您是怎么看待个体口述史的意义的?
A: 细菌战这件事就很典型。在细菌战诉讼发起之前,许多受害者基本上都不愿提及往事。比如衢州的吴世根,因为细菌战失去了自己的姓。他的母亲带着他改嫁,他以前并不姓吴。这种伤痛在他心里是永远也抹不去的。每当过年过节家人聚会的时候,他就会痛哭,把一个原本欢乐的家庭聚会变成一场诉说会。但他的诉说仅限于家庭内部,没有让更多人听到。
常德的这些受害者也是如此。在细菌战诉讼发起之前,他们的诉说会成为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很难有机会去告诉别人自己家遭遇的不幸。
后来细菌战诉讼发起,建立了一个诉说的场域,让像吴世根这样家庭内部的诉说变成了面向社会的诉说。这就形成了一种“记忆场”,个体的记忆由此获得了社会的意义。
我们目前做的口述历史,我觉得就是要将口述作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留存下来。它的价值在于,它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亲历者的讲述,是历史的最小,但最生动的细胞。亲历者讲述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它所涵盖的信息和学者、档案的讲述是不一样的。它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非常生动。当个人的讲述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时,它就有了历史的价值,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Q: 在目前收到的读者反馈中,有没有您印象深刻的一条?作为作者,您又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中读懂什么?
A: 目前收到的反馈还不少,让我感到挺欣慰的。反馈都非常正面,有的人说读哭了,有的人对书中事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想让读者看到什么呢?我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细菌战。中国人在细菌战中付出了百万级甚至千万级以上的牺牲,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关于使用细菌武器会造成怎样创伤的案例。这个案例就是要告诉所有人,细菌战或者其他极恶的战争手段绝对不能在未来发生。如果发生,对人类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牺牲换来的教训,这个教训需要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记住。
Q: 我们对您跟踪报道细菌战23年这件事本身感到由衷敬佩,在您看来,一个记者要对一个选题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报道,这个过程需要哪些条件?
A:我觉得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你自己要去做。你必须认为这件事是重要的,并且要能够坚持不懈。其实,中外像这样做的记者非常多。这并不是说哪家媒体支持你去做,更多时候,是出于个人的主动,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和事业去做的。对我来说,在退休之前我一直是全职工作的,做这件事完全是挤占自己的生活时间,利用业余时间去完成的。
Q: 书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我们认为它也能非常准确地概括记者这份职业的价值观。您能否结合多年的媒体从业经验,谈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A: 这句话是王选说的。作为崇山村的后代,又经历过高等教育,她可以讲英语、汉语、日语和崇山话。只有她能够把这几方面联系起来。因此,她看到了自己的责任,也看到了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记者也是这样的。记者其实是一份天然带有社会责任感的职业,承担着很多社会责任。记者需要关心公共事务,推动社会向更良性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记者也需要具备能力。要在日常工作中把自己做好一件事的能力培养好,总有一天,你就能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事。
(左起)央视纪录片导演郭岭梅,
衢州细菌战原告杨大方、王选、南香红(在衢州采访)
Q: 什么资历的记者才能够去操作像细菌战这样的话题,您建议年轻记者尝试吗?
A: 我觉得年轻记者应该勇敢去尝试。从一开始对选题的关注,到深入了解一个选题,再到试着写一些东西,这其实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年轻记者不一定非得在一年内就写出一部大部头,那不太现实。可以从写好一个小消息开始,学会从消息中提炼新闻要素。之后再逐步接触更长的稿件,对某个话题进行深入研究,最终把它写成一部专著。这条路是一步一步、连续的。
所以,如果年轻人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可以先多读别人的作品,从中汲取经验。然后,尝试着把自己的每一篇稿子写好,从基础做起,逐步提升自己的能力。
(p.s. 1973年,王选考入了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回到义乌成为一名中学教师。1987年,她随夫赴日本留学,在筑波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1995年,王选在《日本时报》上看到关于731部队国际研讨会的报道,让她找到了崇山村想找的两个日本人,这两个日本人曾到崇山村做过细菌战调查。崇山村在1942年曾遭受日军细菌战的荼毒,导致404名村民死于鼠疫,王选家族中也有8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深受触动的王选决定投身于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工作,她放弃在日本的优厚待遇,回到中国开始调查取证。
1997年,王选被推举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团长,代表108名受害者(第二次起诉增到180名原告)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罪行并进行赔偿。经过十年、日本三级法院40次开庭,最终使日本实施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得到法庭的认定。2002年8 月27 日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民事第18 部《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要旨》认定:“根据本案的证据可以认定,旧日本军731部队等在陆军中央的命令下,在衢县、宁波、常德、江山等地将细菌武器应用于实战,并由此使居民感染鼠疫、霍乱,造成多人死亡。这种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的行为违反了日内瓦•毒气议定书,违反了国际惯例,根据海牙陆战条约3条的规定,被告具有国家责任。”此后的中、高级法院均维持这一事实判断,但因两国相关条约和其他理由,驳回原告赔偿道歉请求。
细菌战一审结束后,细菌战的历史被中日两国学界和教育界援引。2005年,日本清水书院将细菌战写入日本高等教育历史教材,这在日本是首次。
王选的坚持和勇气让世界了解日军细菌战的真相。她被《南方周末》《中国妇女》等评为2002年年度人物,并入选“感动中国2002年度人物”。
p.s. 731部队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关东军设立的一支秘密部队,全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代号“满洲第731部队”。它成立于1936年,总部位于中国哈尔滨平房区。该部队以“防疫”为幌子,实际上从事大规模的细菌武器研发和人体实验,包括对鼠疫、霍乱、伤寒等致命病菌的研究和应用。他们对大量中国平民、战俘和苏联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导致数千人丧生。731部队的罪行是二战期间最为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一,其残忍性和危害性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发布于:山西省在线股票配资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没有了
- 下一篇:胜亿优配就像一次恐龙研究学界的聚会